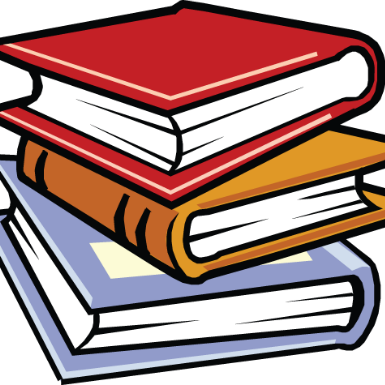一
在某些特定的場合,我覺得自己成功地融入了西方文化。我身邊的女伴有金髮和天藍色的眼睛。我20多歲,不懂愛情,但能辨識旁人目光裡的羨慕;尤其在煙熏火燎的唐人街上,那些緘默然而機警的中國老鄉,眼神猶如一把把鈍銹的菜刀,指向我搖晃的後腦勺和輕狂的下巴。卡特琳偎在我身旁,渾然不覺。她由衷地讚歎著窗後掛的油雞和烤鴨。
這女人比我大5歲,愛好中國菜和東方文化。那年冬天,我放棄了華爾街的薪水和職業,變成一個沒有身份的失業者。周圍幾乎所有人都流露出某種程度的痛惜和不解,甚至輕蔑。而卡特琳朝我張開雙臂,給了我溫暖和愛。
在她的家裡,有迷香、草藥、高纖維的德國黑麵包、兩隻大貓,還有一張高及屋頂的怪床。卡特琳的家鄉是德國巴伐利亞州。她自小叛逆,和父母關係緊張。後來被送到美國讀書,就不再回去。我知道她經歷複雜,有過若干痛苦的記憶。
1989年4月,春暖花開。我和卡特琳的關係出現了麻煩。記得那天在唐人街吃完飯,回家又大吵一架。最後我精疲力竭,上床睡覺。她一個人在廚房裡坐著,幽幽地哭,後來我就聽見她打了個很長的電話。
第二天早晨,我們和好如初。纏綿溫存之後,卡特琳跟我說起約翰·戴維斯,還有南加州洛杉磯北部的一個小公社。總而言之,那兒有幾位我沒見識過的男男女女,他們是卡特琳的好朋友。她正式邀請我去西岸,在朋友們的公社裡住上兩星期。那地方環境特別好,約翰·戴維斯又是一位智慧的長者,說不定,我們的關係能因之而有所改善。
在那個煩躁和傷心的春天,我預感到卡特琳和我終將分手。對於參觀什麼嬉皮士公社,我有重重的疑慮。周圍是一群她的怪朋友,一旦發生什麼分歧或衝突,我將陷於徹底的孤立。最後還是好奇心佔上風,我義無反顧地和她一起去訂了機票。
二
臨上路的頭天晚上,我參加了一個中國人的聚會。那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飯,更像是一個煞有介事的會議。他們目光炯炯,臉孔漲得通紅,還一根接著一根地抽煙,一副捨我其誰的氣派,非一般蔫頭蔫腦的留學生、訪問學者們可比。
在賓州小學院裡讀書的頭兩年,我的生活枯燥至極。我最大的夢想,是能有一天又回到這麼一群牛逼哄哄的北京大哥中間,重溫甚至延續一種越來越遙遠的青春氛圍。後來工作,交女朋友,有了新的煩惱和愛好;那些似乎屬於另一個時空的激動和渴望,慢慢被磨平,淡忘。走進這間屋子,四面轟響著我格外親切又稍有一點隔膜的北京話,血管裡沉睡的細胞開始流淌,甦醒;然而,我的內臟裡似乎增添了新移植的器官,它們無法兼容。我感到無所適從。
我意識到,最近不夠關心時事,錯過了某些大事件。除了感受到空氣裡瀰漫著的憤怒和期待,我並不明白他們辯論的話題。這時,一位老朋友向眾人推介:「這位王先生來美國多年,曾就職於紐約金融界,已融入主流社會。哦,對了!他還有一位德國未婚妻。不妨請王先生談談,西方一般民眾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國。」
這兩個星期,家裡那位西方人士頻頻和我吵架,無論是和她還是她的朋友,都沒有深入討論過中國的形勢。於是我清了下嗓子,支支吾吾地說:不論近期的事件朝哪個方向演變,從根本和長遠的意義上來看,除了少數學者政客,一般西方大眾不會特別在意。說到底,中國不在他們日常生活的視野之內。何至於此?以我個人的觀點,意識形態的品牌化、營銷化,還有生活觀念的極度多元化,可算是重要原因。
看得出,有好幾位臉上露出掃興和不悅。但我還是忍不住多說了兩句:「西方人自己將富裕和自由視為天經地義,很久沒有為之作過流血鬥爭。但社會徹底多元化,各顧各,孤獨和失落,找不著身份和感覺。某一天倘若在思想上、情感上,同一般西方人不再有多少隔閡或距離,其可靠標誌乃是連自己都找不著北了。」
說完我坐下,大夥兒面面相覷。有一位打破沉默:「小王對西方的觀察還算深入、細緻,他提醒大家注意一個現象:相當一批海外華人,未能充分融入西方的上流和主流,容易墜入民族主義的精神洞穴。對此,我們不可掉以輕心……」
我明白自己當了一回反面教材。我做東方人已不夠格,做西方人也挺窩囊。或許,加州的燦爛陽光,將朝我展開大西方另外一片天。
三
約翰·戴維斯和妻子一起來洛杉磯國際機場接我們。他高高的額頭和鼻樑,臉孔渾圓發亮。我無須再追問卡特琳,每次和我吵架之後,那些長電話都打給了誰。
我曾高度懷疑,對卡特琳來說,約翰像一個替代父親、精神導師,還有點曖昧的混合體。這種奇特關係像一團陰霾,籠罩著我們兩人共眠的高床。一見面,約翰的大眼睛迸射出激動、欣喜和憨直,和我緊緊擁抱,專注而且時間長久,似乎要傳遞某種能量。從機場到歐亥鎮車程兩小時。一路上,卡特琳拉著我的手,頭靠在我的肩上。窗外呼呼吹來潮濕的海風,還有棕櫚的清香。前些天我對卡特琳和約翰的陰暗猜疑,無影無蹤,隨風飄散。
那地方和我的想像大相逕庭,完全就是南加州富裕中產者的山地莊園。大草坪、游泳池一應俱全。一打開門,從樓上飛奔下來一個十二三歲豐滿紅潤的小姑娘,她和每人重溫一遍約翰式的擁抱,還在我嘴唇上重重吻了一下。這是麥婭,胖大嫂卓婭的女兒。現在我明白了歐亥公社的見面禮節:充分地擁抱、親吻,以期消除猜疑、敵意,或人性中儲存的其他負面能量。
吃飽了,困了,天也黑了。卡特琳告訴我,在後院樹林子裡有個大木盆,灌上熱水,可以享受星光下的盆浴。胖大嫂卓婭一聽,急急地說也要去。我感到極度困惑和掃興,但不敢流露,畢竟胖大嫂準備了迎接我們的晚餐。況且對公社裡的各種禮節我還不甚了了,也不好意思問得太具體。
洛杉磯著名的廢氣之霧飄不到這山裡。在幾根黑色樹枝上面,淡藍色的夜空如流星雨一般璀璨。那個大木盆,別說三人共浴,恐怕五個人都綽綽有餘。我想得太多了。這裡不忌諱男女一道脫光了身子洗澡或游泳,如此而已。
水蒸氣蒙住了我的眼睛。旁邊的胖大嫂稍稍一動,一股強烈的波浪便湧上我的臉頰。我聽見卡特琳用陶醉的聲調對卓婭說:約翰不是普通人,他能接通宇宙之大能。雖然熱氣逼人,我還是感覺到全身泛起的雞皮疙瘩。
第二天早晨,卡特琳和我兩度纏綿,許久未曾有如此酣暢的親熱和釋放。我攏著她汗濕的頭髮,心中湧出無與倫比的柔情。「我愛你!」我對她說。她沉默良久,用她的藍眼睛注視我。我從那眼裡看見從未見過的冰冷。「我不能再愛你了,」她說,「我有病,還在康復之中;我得先學會愛自己。」
四
我克制住了提前返回紐約的衝動,硬下心腸在讓我心碎的歐亥伊甸園裡住滿了15天。我搬到大宅子的另一角,強忍著溢滿胸腔的委屈和傷感,每天找些方法來打發時間。
在公社,我認識了沃夫岡和他的美國女友妮娜。沃夫岡也是德國人,據說從前是西德學生運動的激進左派,拋下妻小,一個人跑到加州。每天和他們閒聊,我慢慢瞭解了歐亥公社所代表的一些學說和主張。大概意思是:在每個人的身體和潛意識深處,都埋藏著巨大的能量,通向無限的生命和宇宙之大愛。尋常世人的喜怒哀樂、情感欲求通通不值得重視。多數人一生辛勞求索,悲喜輪迴,無止無息。那麼,如何找到那個能量呢?答案是:慢慢學會愛自己。當然,約翰可以給予某些指導。
「約翰·戴維斯是好人。」沃夫岡說,偶爾有朋友來此地小住,有錢就給點兒,沒有也不計較。戴維斯原來是骨科醫生兼康復專家,後來有個好萊塢過氣女星給了一筆數目可觀的捐助,從此他行醫兼心理咨詢並布道,還享受一小批人源源不斷的追捧。沃夫岡還說,在陽光燦爛、內心空虛的南加州,像戴維斯這樣的小教主不在少數。
歐亥公社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個絳藍色的游泳池。無聊的下午,我去游泳池,沃夫岡和妮娜總在那裡。於是,在清得發亮的水裡,兩個赤條條的大男人,有時加上抱著塑料鴨子的小麥婭,來來回回地穿梭游動。妮娜始終躺在大毛巾上讀流行小說。每次轉變方向,我試圖不朝她的方向看,以免過分注意到刺目陽光下她袒露無遺的身體。
當時我想,能當上戴維斯這樣一個滿面紅光、招人喜歡的大騙子,實在是一種不錯的活法。
臨走前兩天,卡特琳幫我跟戴維斯約了時間。白天他忙,約在深夜。我們坐在大木盆旁邊,看著遠處的山脈和星星。出乎意外,他對我和卡特琳的傷心史毫無興趣,倒問了很多涉及中國的問題,關於我如何長大、與父母怎樣相處,等等。他還問我如何看待美國的自由。我反問:「你怎樣看呢?」他回答:「美國人有各種法律權利,但毫不自由。因為他們缺乏感覺的自由,要別人來教,才曉得怎樣開心、怎樣給自己找樂。」世上有這麼蠢的人嗎?
分手了。我和約翰·戴維斯緊緊擁抱。他不經意間講了一聲:「聰明小伙兒,找個別的女孩罷,容易得很。」
五
20多年過去了,卡特琳和我建立了比較持久的友情。有一年我情緒低沉,約她一道吃飯。我告訴她決定放棄綠卡,返回中國。卡特琳未表示絲毫的不解或驚訝。
不出幾個月,我從北京打國際長途給她,我已徹底變卦,終歸不能適應在中國長住。卡特琳開心地哈哈大笑,沒有任何藐視或嘲笑的意思。
那年在紐約一道開會的年長朋友,直至今日,仍然學不會或不肯學會英語,還繼續憤憤不平地議論著與當初相似的話題。